詩性即神性(自序)
詩性是一種神性
大多數(shù)人都在用感官來理解世界��,于是他們看到的是無垠的宇宙和相比之下渺如塵埃的自己��。同時��,人類在努力讓自己的世界變得可控和可預測��,但在如此浩瀚的宇宙中��,似乎永遠也無法實現(xiàn)��。也正因如此��,他們把自己形容為塵埃��。這種浩渺��,沒有讓他們體會到回旋的余地之足夠充分的歡愉��,相反��,帶來的卻是安全感的極度缺乏。
于是��,一部分人選擇對神祇無條件地信仰��,以此讓世界看起來是有終極的邊界的��,因此獲得足夠的慰藉��。而另一部分人��,選擇了去思索世界的終極規(guī)律��。因為假如找到了終極的規(guī)律��,世界就不再是無限和不可控的��,而只是規(guī)律下展現(xiàn)的無限列舉��。這就是哲學��。
哲學要尋找的答案是唯一性的��,就如同孩子們玩的拼圖��,或者積木��。他們認為��,這個世界無論以何種方式被打亂��,背后總有一個唯一的說明書��,能按照它重新恢復��,變得完整而有序��。這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核心動力��。
所有這些努力��,都在讓人類逐步進步��,不再因無限性��、不可控性而處于缺乏安全感的狀態(tài)��。但問題在于��,越是證明世界的規(guī)律��,越讓我們疑惑是誰締造了這種規(guī)律��,于是哲學和神學就有了交集。在這背后��,人自身并沒有因為規(guī)律強大起來��,相反��,他們被粘連在規(guī)律上��,更顯得被動��、渺小而無助��。
但詩性作為所有藝術(shù)的核心��,恰恰走上了相反的道路��。這種相反��,不是用詩性反對理性的建構(gòu)��,而是詩性放任世界的無限性��、不可控性��,并把它當作一種積極的事實��。由此感受到回旋的余地之足夠充分的歡愉��。
他們的努力不在于用唯一穩(wěn)定存在的規(guī)律或秩序消除這種無限感和不可控感��,而是走了另一條道路��,即尋找世界的原點��,也就是出發(fā)點��。這個原點��,可以輕易讓世界沉浸在一種秩序中��,變成穩(wěn)定的��、有序的存在��,這表面上與哲學是相通的��。但不同的是��,這個原點在詩性的理解中��,一旦達到了類似的效果��,就會被擱置,然后又會在下一次創(chuàng)作中��、下一個作品中��,尋找新的原點��,仍然重新整合這個世界��。最后��,這個原點在無數(shù)作品里就表現(xiàn)為是任意選取��。
哲學始終要尋找的是外在世界的唯一答案��,而詩性則要通過對人的內(nèi)在精神求證��,人在世界中究竟是處于主動還是被動的地位��。
詩性讓他們獲得了什么呢��?恰恰獲得的就是對自身生命的存在的確認��,即滿足于世界的無限性��,再通過人整合能力的無限��,轉(zhuǎn)換成人的無限性,因此與世界的無限性相匹配��。這種無限性因此不再是一種被動的無限性��,而變成了人的主動性和主控性的事實��。
由此��,世界可以是無限的��,但又隨時能夠被征服��,按照詩性的發(fā)現(xiàn)而總能重新整合起來��。而可以按照無數(shù)的方法征服��,否定了哲學的唯一性��,又證明世界仍然是無限的��,但這種無限��,則已經(jīng)是強調(diào)人自身的無限性的證明��。他們可以用無限種方法��,讓世界呈現(xiàn)無數(shù)種完整而完美的狀態(tài)��。因而瞬間就把哲學的如履薄冰��,變成了人本身游刃有余的自由��。
通俗地來說��,詩性的創(chuàng)作者是所有哲學家的集合��,他們隨時讓作品呈現(xiàn)一種哲學��,又會在下一首作品中��,變成另外一種全新的終極架構(gòu)��。但他們不會讓自己變成哲學家��,去篤定地相信世界是拼圖或者積木��,有唯一的說明書��。因為這讓人獲得安全感的同時��,也喪失了終極的自由��。而藝術(shù)是通過無限種哲學,讓自己變成世界之駕馭者��,以此說明人的自由自在��。
而更重要的是��,人的情感本身也成了立足點��,作為整合世界的原點所在��,這大大超越了哲學本身所能做到的��。
所以��,一個真正秉承詩性的藝術(shù)家��,是度過了有拼圖��、積木的童年時代的成年者��。你一定會不約而同地和我一起說出:這樣的詩性其實就是神性��。
是的��,詩性就是神性��。人憑借詩性本身��,就有了自身的神性��。一個憑借詩性而存在的人��,像神一樣��,隨時駕馭世界��,又隨時放任世界��。因為他隨時可以重新用一種方法��,拯救世界��,讓世界有更好的秩序��。因此��,世界的無限性和不可控性��,只是他表演的道具��,以此來襯托和證明神性自身的偉大。而藝術(shù)��,就是人性通向神性的階梯��。與所有普通人相反��,他們不僅不會因為無限性和不可控性而感到恐懼和憂傷��,恰恰會因此感受到生命對它的駕馭之無限活力��。
所以��,詩性就是對世界無限地去整合��、無限地去締造��、無限地去自主的唯美存在感��。一種摘花捻葉的自由��、自如��、自主之存在方式��。
之所以在這里加上唯美��,原因就在于��,如果真善美不是一個詩性的人唯一的締造和整合的方向��,那么他的詩性就會成為與神性相反的魔性��。
神性與魔性
既然談到神性��,那么對立的就是魔性��。神性有自己的精神內(nèi)核��,成為神性與魔性的根本區(qū)別��。
神性的第一要素��,就是創(chuàng)造��。
這種創(chuàng)造��,神性自身已經(jīng)體現(xiàn)��。即永遠不會墨守成規(guī)��,并去證明這世界雖然無限��,但是卻可以以任何一個點為原點,按照詩性的方法重新組織��,讓世界呈現(xiàn)出完美而積極的形態(tài)��。也就是��,假設(shè)有終極的上天��,設(shè)定了我們公共的感知的世界��,那么人的神性要做的��,就是在這面鏡子里��,借著人類自己的光芒��,讓世界呈現(xiàn)一種光輝的形態(tài)��。人換了一個地方��,換了一個角度��,就會照見不同的風景��。而不是相反地��,讓這面鏡子只能照見永恒的黑暗��,永無差別��。
所以��,這要求你不斷去創(chuàng)造��,用自己的光芒��,在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照亮別樣的世界��。于是世界就呈現(xiàn)萬般不同的風景��。
神性的第二個同等重要的要素��,就是拯救��。
如果一個神��,不去拯救��,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��,只是廟堂中的泥胎��。神性是人類自我期待的神性,它首先是拯救自己��,那個陷入瑣碎��、片段��、無意義的自我��,那個驚恐��、茫然的自我��。然后以此喻示:陷于黑暗和枷鎖中的人類��,可以借此獲得拯救��。
神性的第三個同等重要的因素��,就是唯美的方向��。
這種美��,通常是人類文明共同認可的方向��。它其實是真善美不可割裂的復合存在��。正是因為這個原則和尺度��,讓神性和魔性得以區(qū)分��。
魔性總是相反的存在��,與人類認可的美好價值相反��,他們要證明毀滅才是人的價值��,以此來證明所有的真善美都是幻想��,而最真實的只是自我的摧毀力��,也就是純粹的暴力��,他們崇尚的是運用這種摧毀來實現(xiàn)個人對世界的終極統(tǒng)治��。
而這種統(tǒng)治的路徑��,就是打碎上天的鏡子��,讓人類永遠無法見到光芒��,只能看到自己塵埃一樣的瑣碎��,但他自己壟斷了讓世界整合的能力。所以這是一種無法逆轉(zhuǎn)的邪惡��。
綜上所說��,作為藝術(shù)的核心詩性��,能被稱為神性��,就在于啟發(fā)人們?nèi)フJ識到自己的神性��,從而每一個人都可以點亮自己��,去照見世界不同的風景��。
或者��,即使人們還是不夠自信��,不相信自己可以駕馭��,那么就借給他們光亮��,讓他們看到世界總是璀璨地呈現(xiàn)在他們面前��。
詩性在人性中的淪落
今天,我們可以讀各種各樣的詩歌��。
通過一首詩歌��,你可以依稀看見詩作者的形象��。
有的詩中��,你看見一個詩人正穿著夏天的短衣短褲��,邊坐著乘涼閑聊��,邊搖著蒲扇��。他正漫無邊際地說著他一生的奇遇��,從張三的早飯?zhí)S到海南的東郊椰林��,永不疲倦地嘮叨著那些無窮無盡的瑣碎��。
有的詩中��,你看見一個詩人穿著粗布衣衫��,在街頭巷尾不停地謾罵��,不停地發(fā)泄著不滿��。他們的確足夠刻薄��,可以把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物事��,指摘得一無是處��,而且充滿智慧��。但你若問他們��,到底什么是他們欣賞的��,他們總要告訴你��,我的義務不是欣賞��。
有的詩中��,你看見某個詩人穿著雍容華麗的禮服��,正在參加一場宮廷舞會��,他們優(yōu)雅而禮貌地在人群中穿梭��,無論音樂怎么變換節(jié)奏,都不會亂了頭發(fā)和舉止��。
是的��,自古詩人就一直被人們所尊重��。那是因為詩人們累積的神性光輝所使然��。但今天��,太多人自命為詩人��,在努力消費這種遺存的光芒��。他們其實比任何普通人都要市儈��。他們已經(jīng)徹底喪失了詩性��,喪失了神性的風骨��。
期待的樣貌
我希望��,在我的作品里��,讀者看不到我的具體面貌��。他只能看到作品中構(gòu)筑的世界��。他唯一能感受到我存在的方式��,就是發(fā)現(xiàn)有一束光芒照亮了詩中一個別樣的世界��。
他們借著這束光芒��,看到了世界這面鏡子里��,被照亮的絢麗景象��。
我不在于通過作品��,讓讀者確認我像神一樣的存在��,而是啟發(fā)所有人��,在讀過很多充滿光線的作品后��,意識到這個世界有無限的方法可以重新打開��,意識到他們自己也可以讓世界重新燦爛地打開��,他也曾經(jīng)用自己的方式照亮過這世界��。
因為,人性借由詩性而獲得自由��。所以獲得詩性自由的人��,都可以意識到自己神性的存在��。那就是我要再次強調(diào)的��,詩性就是對世界無限去整合��、無限去締造��、無限去自主的唯美存在感��。
而我發(fā)現(xiàn)這些��,創(chuàng)造這些��,僅僅是因為我也曾經(jīng)在人間沉淪��,在無限墮落的恐懼中��,終于用詩性拯救了自己��。我用自己的光芒��,重新照見了世界無限的風景��,從而確認了詩性偉大但卻并非高不可攀��。只要一個人不放棄自己��,就會被任何一條線索拯救��,因為這個世界終極的存在具有完美的本性��,所以它才能無限而永恒地存在下去��。
是的��,我必須用詩歌和詩性告訴大家這些歷程��。
我在你們所想象的地獄之中��,因囚禁的重壓而爆發(fā)��,讓自己燃燒為熔巖��,最終噴薄到人間��,成為雄渾的高山��。而我在人間自由穿行的時候,在每一片葉子背后��,在每一粒黃沙的軌跡中��,總能翻閱到天堂的扉頁��,從而發(fā)覺了它無處不在的親近��。
所以��,我并不急于想在詩中表達我自己是什么樣子的��。我更愿意��,表達那些用我自己的生命所照亮的世界是多么透徹而清亮��。而每一個婉轉(zhuǎn)和黯淡的角落��,都在于揭示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拯救自己��,一轉(zhuǎn)身��,就可以看到黎明的煦暖��。是的��,我期待著所有人不僅僅看到作品所塑造的世界里的光線��,更能看到你自己可以在作品的世界里存在著��,發(fā)現(xiàn)這些文字本身��,它們發(fā)不出光芒��,但卻可以點燃你自己��,照亮這個世界里的每一個角落��。
這就是詩人唯一要做的��。
不是為自己樹碑立傳��,而是歌頌詩性與神性��,它們就在每一個人的人性之中一直存在著��。
這就是人活著的終極意義��。
它不是自輕與自賤��、懦弱與悲哀��,而是創(chuàng)造與拯救、自由與愉悅��,無論對于自我還是對于世界而言��。
錯河
2017年9月21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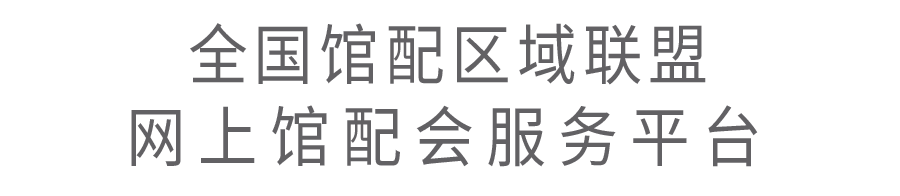
 書單推薦
書單推薦 新書推薦
新書推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