筆名野馬�����,史家�����,作家�����,書畫家�����,瓷藝家�����。潮汕人�����,壯歲漫游江南�����、荊楚�����、巴蜀�����、京畿�����,客居杭州十二年�����,在景德鎮(zhèn)御窯遺址公園佛印湖畔開設(shè)“野馬堂陶瓷藝術(shù)工作室”�����。個人微信公眾號:異史氏�����。
在《讀書》《人民文學(xué)》《詞刊》《天涯》《北京文學(xué)》《南方周末》《西部》《作品》《星星》《浙江詩人》《博覽群書》《□□文匯》《品位·藝術(shù)空間》等刊物發(fā)表文學(xué)藝術(shù)作品和學(xué)術(shù)研究成果;在杭州�����、廣州�����、北京等地舉辦“貓民代表”“過隙·有貓”個人書畫展及插圖展�����;出版有《提頭來見:中國首級文化史》《帶著花椒去上朝:古殺十九式》�����,即刊有《人中呂布:中國養(yǎng)子文化史(上編)》(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(lián)書店)�����、《周旋之死:出南朝記》(讀庫策劃�����,新星出版社)�����,插畫有《我有一只貓�����,足以慰風(fēng)塵》(哈爾濱出版社)《你生活的樣子�����,就是你靈魂的樣子》(北京時代華文書□)�����。
10. 潮汕人怎么喝路易十三
常常�����,故鄉(xiāng)稻浪金黃�����,低樹青黛�����,遠處江海際天�����,無限蔚藍�����;偶爾�����,故鄉(xiāng)是一片金亮金亮琥珀紅�����。
我非作詩�����,我想起酒——洋酒:干邑蒸餾烈性葡萄酒�����,以及它們布在鄉(xiāng)黨之口的品牌或指認:人頭馬、大將軍�����、軒尼詩�����、路易十三�����、藍帶�����、金花�����、長頸�����,乃至無上李察……
一部潮汕的歷史�����,就是“道統(tǒng)”與“盜統(tǒng)”你中有我�����、移步換形的交互史�����。我由海盜思及曹操�����,由觀滄海想到萊蕪渡�����;我在土豪�����、劍客與豪情逸興�����,精鄙與優(yōu)雅,性情與功利的交織中�����,聞到牛田洋�����、廣澳灣海風(fēng)中路易十三�����、杯莫停的醇香�����;兒時的紅泥小爐炭響泉沸�����,我從工夫茶的氤氳香氣�����,想到□□□鮮能體驗的“圍鵝夜酒”,想起汕頭市區(qū)長平路那食客川流錯踵的通宵燈火夜粥攤檔上冷不丁就出現(xiàn)在某張簡陋餐桌的軒尼詩臂握戰(zhàn)斧商標�����,甚至是那□□巴卡拉玻璃廠手工打造的□□水晶玻璃酒瓶�����。
從甜釀喝到藥酒�����、果酒�����,八竿子奈果打著個星期日痛風(fēng)�����,本來該打住�����,轉(zhuǎn)說茶——是個潮汕人都天生默認�����,茶才是潮汕的炊煙�����、潮人的里子和血液——可我那被激活的故鄉(xiāng)記憶竟自動開啟魔幻�����,如萬花筒不斷旋轉(zhuǎn)�����,由藍而黃�����,而褐而朱�����,而琥珀�����,一點菩提,泊入赤霞�����,澄于金亮�����。我突然就明白�����,今日寫潮汕浪話�����,捫摩潮人氣質(zhì)�����、潮汕味道�����,已然繞不開色如琥珀的陳年洋酒�����。前朝舊日豬仔悲歌�����、水布傳奇�����、僑批音書以至紅頭船�����、暹羅米�����、風(fēng)油精�����、咸水表層層疊疊的模糊影像之上�����,是新□、矗起的海岸樓群�����、高速鐵路�����、跨海大橋……今日之浮世繪里�����、名利場中�����,人們推杯換盞�����,壯懷逸興�����、言笑晏晏或真或偽�����,亦正亦邪�����,而澄海鵝肝�����、普寧豆干們已在干邑玉液�����、北美冰酒的舌尖化蝶�����,潮陽麻葉�����、潮州打冷也每與飛天茅臺�����、五糧水井、劍南瀘州們物色親近�����。
如是�����?如是�����,如如是�����。
靜言思之�����,從前潮汕之非酒國醉鄉(xiāng)�����,既緣省尾和暖�����,亦因國角人貧�����,善茶刮胃(嗜茶而茶性消食過甚�����,腹中油葷盡而饑)�����,研酒乏鐳(錢也)�����,并不說明潮汕人缺少野性�����,臨杯無量�����,與酒不親。
宋明以降�����,潮汕社會雖形成以儒家禮教為主導(dǎo)的鄉(xiāng)村治理系統(tǒng)�����,發(fā)展出精耕細作的農(nóng)業(yè)經(jīng)濟�����,然天風(fēng)濤海一直是族群底色�����、文化精神�����、地緣活力�����。潮汕與海外——主要是東南亞的商貿(mào)與□□自成循環(huán)�����,非海禁遷界�����、閉關(guān)鎖國所能遏止�����。
消極而言�����,行船走馬三分命�����,尤其在大陸文明絕對強勢的封建王朝�����,每視巨洋為盜藪,海商如寇倭�����。討海過洋的族群�����,正當借酒壯氣�����,食死浪歇(吃光拉倒)�����,今朝有酒今朝醉�����。
積極而論�����,海洋文化崇尚冒險�����,擲杯煮海,不主一成�����,不囿一地一國�����,五洲四海一碗酒�����。山有窮處�����,水無盡頭�����,“一條水布下南洋”“食到無�����,過暹羅”�����,實要有“家無擔(dān)石之儲�����,樗蒲一擲百萬”(《晉書·何無忌傳》桓玄評劉毅之語)的血勇墊底�����。故以精神氣質(zhì)論�����,潮汕人必能破立�����,敢賭好飲����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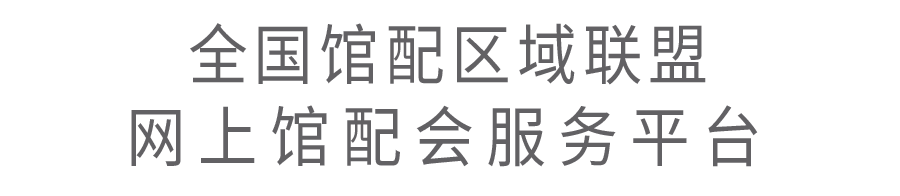
 書單推薦
書單推薦 新書推薦
新書推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