±ŸűŐçßx14ÆȘÓÉűÈ(nšši)W(xušŠ)Őߌ«”Ä·ŚgŃĐŸżŚśÆ·, ŚśŐß»òÍšß^ŠvÊ·ŐZŸł”Äă^łÁ, »òÍšß^żçÎÄ»ŻvÊ·ÎąÓ^(shšȘ)ŚC·ÖÎö, »òÍšß^ŠÎıŸÁxÀíÔ~Ő”ĜâÎö, Êč·Śgß@öÀâçRËùŐÛÉäłöȻ͏”ÄÉ«ČÊ, ŒÈÓжŰïL(fš„ng)»ŻËŚ”Ä(shšȘ)Û`čŠÓĂ, ÓÖÓĐâùÇéž”ČÊ”ÄĐȚÉíЧÄÜĄŁ
ŁÚŁșÖĐű·ŚgÊ·ŃĐŸż
ÍőșêÖŸ©Š ÖśłÖÈË”ÄÔ
àżÆ©ŠÇćÇ°ÆÚ¶àŐZÎÄŐțÖÎÏ”ÄŐZŃÔčÜÖÎĆcĄ°·ŚgĄ±ŚRœâ
ÇfńYÔ©Š ÒÔŚgŽúÖű ÈÚÍšÖĐÎśĄȘĄȘÀ(yšąn)Í(fšŽ)Ą¶·šÒ⥷ŠĂÏ”ÂËčűFŐțówW(xušŠ)Őf”Ä·Śg
ÀîŒŃ„©ŠűĄß\(yšŽn)Ó”ÄÒ»ŽÎĄ±Ÿ(shšȘ)Û`ĄȘĄȘĄ¶éLÉúÔEĄ·”Ä·Śg
ÎÄW(xušŠ)·ŚgĆcżçÎÄ»ŻŃĐŸż
ÛŹÔȘ©ŠÂÔŐfôŃžĄ¶Ò°ČĘĄ€ÇïÒ襷Ą°ÆæčÖ¶űžßĄ±Ą°Òč°ë”ÄĐŠÂĄ±Ą°ĐĄÇàÏxĄ±
¶ÎŃÇć©ŠčŒűăŁșĄ¶°VhòTńRžèĄ·Œ°ÆäÖÜú
ČÌŃĆÖ„©Šß
Ÿ����ĄąËûŐßĆcÈÚșÏĄȘĄȘŐČ© șŐËčŠĂśÇćĐĄŐf”ÄœÓÊÜĆcêUá
ŽȚ·ć üSÜ°x©ŠŐĐÂŒÓÆÂĄ°șúŒ§»šĄ±”Ä·ŚgčŠÄÜŒ°ÆäÉçțÎÄ»ŻÙĐÔ
·ŚgĆcżçW(xušŠ)żÆŃĐŸż
ÍőșŁ OÒ»șŐ©ŠĄ¶ÖĐűóW(xušŠ)Ê·Ą·ÍâóŚgĂûĆcÊ·(shšȘ)ŚgœéŃa(bšł)Őę
îìÌ©Š Ą°êÓ°Ą±ĆcĄ°ÓÍÄàĄ±ĄȘĄȘűëH·šà(qušąn)ÍțÔÚ19ÊÀŒo(jšŹ)ÖĐű”ÄŚgœéĆcÖŰËÜ
·Śg(shšȘ)Û`ÌœËś
ž”Á©ŠĄ¶íčâÄżĄ·ŁšŁšDhvanyšĄlokalocanaŁ©”ÄŚgĆcáŁšÒ»Ł©ĄȘĄȘŒæŐèóŐZŐÜW(xušŠ)?šĄstricŁ©ÎÄ«I(xiš€n)”Ä·Śg
ÍőÀíĐĐ©ŠÖÒ(shšȘ)ĄąÍšíĆcĄ°č«čČĐÔ”ÄŐZŃÔĄ±ĄȘĄȘĆcŒsșČĄ€È(nšši)ɔĥ¶ÖÒ(shšȘ)ĆcÍšíżÉŒæ”ĂŃÉ����ŁżĄ·čČűQ
ŃĐŸżÉúŐŻ
ČÜçśÁŐ©ŠÔÈËŚgÔ”ÄĂ}œj(luš°)»ŻżŒČì
ŐśžćąÊÂŁšCall for PapersŁ©
ĄŸÎÄŐȘĄż
ÎÄŐȘÒ»Łș
Ą°ÖĐű·ŚgÊ·ŃĐŸżĄ±ŁÚŁșÖśłÖÈË”ÄÔ
ÍőșêÖŸ
±ŸĘĄ°ÖĐű·ŚgÊ·ŃĐŸżĄ±ŁÚżŻłö”ÄÈęÆȘŐÎÄ����ŁŹ·ÖeÉ挰žĆÄîÊ·ĄąËŒÏëÊ·șÍÎÄW(xušŠ)Ê·����ŁŹłä·Öï@ÊŸłö·ŚgÊ·ŃĐŸż”ÄżçW(xušŠ)żÆÌŰÙ|(zhšŹ)ĄŁ
àżÆ”ÄĄ¶ÇćÇ°ÆÚ¶àŐZÎÄŐțÖÎÏ”ÄŐZŃÔčÜÖÎĆcĄ°·ŚgĄ±ŚRœâĄ·ŚąÒ├·đœ(jš©ng)·ŚgÖźÍâ”ÄÖĐűčĆŽú·ŚgÊ·ŁŹ¶űÇÒąÄżčâŸÛœčÓÚÒÔÍùêP(gušĄn)ŚąĘ^ÉÙ����Ąą(shšȘ)tÓÈéÖ””ĂÉîŸż”ĶàŐZŃÔ»ìës”ÄÇćŽúŁŹŠż”ÇŹrÆÚĄ°·ŚgĄ±žĆÄî”ÄÈ(nšši)șŒ°Æ䱳șó”Ä·ŚgŐțČß”ÈÉçțÎÄ»Ż±łŸ°ŚöÁËÊáÀí���ŁŹżÉÒÔŐfŃa(bšł)ÁËÖĐű·ŚgÊ·ŃĐŸż”ÄÒ»ŽóżŐ°Ś���ĄŁŚśŐßłä·ÖÀûÓĂÖĐÍâÎÄ«I(xiš€n)ĄȘĄȘÌŰeÊÇ°l(fšĄ)ŸòÁËČ»ÉÙ·ŚgŃĐŸżÏàêP(gušĄn)”ÄMÎÄn°žŁŹČąœèèbÓ(jšŹ)ÁżÊ·W(xušŠ)șÍÔ~ÔŽżŒț(jšŽ)”ÄŃĐŸż·œ·š����ŁŹÊÇÒ»ÆȘÏàź(dšĄng)Ôú(shšȘ)”ÄÎÄŐÂĄŁ
Ä·ŚgœÇ¶ÈżŒČìœüŽúÖĐű”ÄÖȘŚRÓ^ÄîȚD(zhušŁn)ĐÍoÒÉÊÇÒ»í(xiš€ng)ÖŰÒȘ”Ä·ŚgÊ·Őnî}���ĄŁÇfńYԔĥ¶ÒÔŚgŽúÖű ÈÚÍšÖĐÎśŁșÀ(yšąn)Í(fšŽ)ĄŽ·šÒ⥔ŠĂÏ”ÂËčűFŐțówW(xušŠ)Őf”Ä·ŚgĄ·���ŁŹÒÔÀ(yšąn)Í(fšŽ)ŠĂÏ”ÂËčűFŐțówW(xušŠ)Őf”Ä·Śgé°žŁŹżŒČìÎś·œœ(jš©ng)”äŐțÖÎW(xušŠ)ËŒÏëŚgÈëhŐZß^łÌÖДĞďF(xiš€n)Ïó����Ł»ČąœY(jišŠ)șÏ20 ÊÀŒo(jšŹ)łőÖĐű”ÄÉçțvÊ·ŐZŸłŁŹÌœÓß@Đ©·ŚgžÄ”ÄËŒÏëÊ·ÒâÁx���ŁŹČ»HÍŰŐčÁËŹF(xiš€n)ÓĐÀ(yšąn)Í(fšŽ)·ŚgŃĐŸż”ÄêP(gušĄn)ŚąÒÒ°����ŁŹÒČœÒÊŸłöÖĐűœüŽúW(xušŠ)Đg(shšŽ)·ŚgŚśéÖȘŚR(chuš€ng)Ôì”ÄÌŰĐÔĄŁ
ÀîŒŃ„”ÄĄ¶űĄß\(yšŽn)Ó”ÄÒ»ŽÎĄ±Ÿ(shšȘ)Û`ĄȘĄȘĄŽéLÉúÔEĄ””Ä·ŚgĄ·êP(gušĄn)Śą”ÄÊÇÖĐűòĄÀíŐŒÒÓàÉÏăä·Śg”ÄĄ±ŸĄ¶éLÉúÔEĄ·����ĄŁĄ¶éLÉúÔEĄ·ÊÇœĘżËŚśŒÒżšÀŚ Ą€ÇĄĆćżËŁšKarel ?apek����ŁŹ1890ĄȘ1938Ł©ÊŚ±»ŚgłÉhŐZ”ÄĄ±ŸŁŹÊÇœĘżËÎÄW(xušŠ)ÔÚÖĐűœÓÊÜ”ÄÖŰÒȘ°ž���ŁŹ”«ŽËÇ°ÎŽÓĐŁÎÄŐŒ°����ĄŁŚśŐßÍšß^Œ(xšŹ)Ö”ÄÎıŸ·ÖÎöșÍÊ·ÁÏœâŚx���ŁŹŚąÒ├ÓàÉÏă乥°ÔĄĄ±ź(dšĄng)ŚśŠżčÒŚČ·ÉúòĄ”ÄÒ»·NÊֶΥȘĄȘß@ÊÇŠŹF(xiš€n)ÓĐÓàÉÏăäòĄËŒÏë”ÄÖŰÒȘŃa(bšł)łäĄŁŚśŐßß°l(fšĄ)ŹF(xiš€n)Ą¶éLÉúÔEĄ·(shšȘ)Û`ÁËűĄß\(yšŽn)Ó(shšȘ)éűĄËŒÏëÔÚĄ±ŸÓĂæ”ÄŸßów»Ż���ŁŹÓĐÖúÓÚÒÔß\(yšŽn)ÓÔÚ20 ÊÀŒo(jšŹ)òĄŹF(xiš€n)Žú»ŻßM(jšŹn)łÌÖĐ”ÄvÊ·”Űλ���ĄŁ
ĄȘĄȘĄȘĄȘĄȘĄȘĄȘĄȘĄȘĄȘĄȘĄȘĄȘĄȘ
ÎÄŐȘ¶țŁșč(jišŠ)ßxŚÔŁș
ÂÔŐfôŃžĄ¶Ò°ČĘĄ€ÇïÒ襷Ą°ÆæčÖ¶űžßĄ±Ą°Òč°ë”ÄĐŠÂĄ±Ą°ĐĄÇàÏxĄ±
ÛŹÔȘ
Ą¶ÇïÒ襷żÉŐÖźÌÉő¶à���ŁŹ±ŸÎÄŸÛœčĄ°Íâ”䥱ŁŹÔéÔáÈôžÉvíëyœâÖźÔ~ŐZ���Ą����ŁĄ°ÆæčÖ¶űžß”ÄÌìżŐĄ±���ŁŹß@ÆæáÈ”ÄÇČÔ~ÔìŸäÔÚôŃžÖűŚśÖĐČąoĄ°È(nšši)”䥱żÉ€���ĄŁŒsÂÔÏàœü”ÄÖ»ÓĐôŃžËùŚgșÉÌmŚśŒÒÍûĄ€Ì@ńûŁšFrederik von EedenŁ©Ą¶ĐĄŒsșČĄ·ŁšDer Kleine JohannesŁ©”ÚŸĆŐ”ÄÒ»ŸäÔŁș
ÔÆ”ÄÖĐégŁŹșÜžß���ŁŹÆæč֔Ğß���ŁŹËûżŽÒÇćÀÊ”ÄÄęčÌ”ÄΔË{(lšąn)ĄŁ
Ą°șÜžß����ŁŹÆæč֔Ğߥ±���ŁŹ ôŃžËùț(jšŽ)Anna Fles ”ĔŒg±ŸDer Kleine Johanness éviel höher, unendlich hochŁŹżÉÖ±Śg饰șÜžß”Ä����ŁŹoÖčŸł”ÄžßÌĄ±ĄŁôŃžï@È»ČÉÈĄÒâŚg���ŁŹÔöŒÓÁË”ÂŐZÔÎÄËùo”ÄĄ°ÆæčÖĄ±Ò»Ô~����ĄŁÓĐÈËț(jšŽ)șÉÌmÎÄÔ±ŸŚgŚśĄ°șÜžßșÜžß���ŁŹžß”Ăßh(yušŁn)Č»żÉŒ°”ÄÄǔ۷œĄ±���ŁŹœÓœü”ÂÎÄŚg±ŸĄŁÓąŚg±Ÿévery,very high up����ŁŹÌÀí”ñÈĘ^șÎĄŁ
”ÂÎÄ���ĄąÓąÎÄ���ĄąșÉÌmÎÄÖĐŚg±ŸÂÔÓĐČŹ”«ŸùoĄ°ÆæčÖĄ±Ò»Ô~����ĄŁUnendlichŁšĄ°oÖčŸłĄ±Ą°o±Mî^Ą±Ł©ÊÇ€łŁ”Ä”ÂŐZĐÎÈĘÔ~ŁŹ°ŽÀíČ»țŚgće����ŁŹ”«ôŃžéșÎÆ«ÒȘŚgłÉĄ°Ææč֔ĥ±ŁżÊÇ·ńÓĐÒâÄŁ·ÂÏČgÌœËśÎŽÖȘ¶űÓÖÈĘÒŚó@Ó ”ÄșÍŻĐÄÀíĆcșÍŻŐZŃÔ���ŁżoŐÈçșÎ����ŁŹß@Ó”ÄÒâŚgÁÔÆ”ÄÖĐég����ŁŹșܞߣŹÆæč֔Ğߥ±șÍĄ¶Ò°ČĘĄ·Ą°ÆæčÖ¶űžß”ÄÌìżŐĄ±°l(fšĄ)ÉúÁËÓĐÈ€”Ä»„ÎÄŹF(xiš€n)Ïó���ĄŁ
Ą¶ĐĄŒsșČĄ·ôŃžŚg±Ÿ”ĔڟĆŐÂßÓĐÒ»ÌîËÆ”ÄŚg·š���ŁŹżÉÒÔŚôŚCĄ¶Ò°ČĘĄ·Ą°ÆæčÖ¶űžßĄ±ĆcĄ¶ĐĄŒsșČĄ·Ą°șÜžß����ŁŹÆæč֔Ğߥ±Öźég”ÄêP(gušĄn)Â(lišąn)ĄȘĄȘ
Der Himmel war schwer und schwarz.
ôŃžÖ±Śg饰ÌìżŐÊÇÖ۶űșڔĥ±���ŁŹî”čß^íŸÍÊÇĄ°Ö۶űșÚ”ÄÌìżŐĄ±����ŁŹœüËÆÓÚĄ°ÆæčÖ¶űžß”ÄÌìżŐĄ±����ĄŁżÉÒÔÚŚgŚśĆc(chuš€ng)ŚśÖĐ���ŁŹôŃž¶ŒîHéÆ«ÛĄ°șÜžß����ŁŹÆæč֔Ğߥ±Ą°ÌìżŐÊÇÖ۶űșڔĥ±Ą°ÆæčÖ¶űžß”ÄÌìżŐĄ±ß@Ò»îŸäÊœ���ĄŁ
ôŃž1926 ÄêÏÄëxé_±±Ÿ©ÖźÇ°���ŁŹČĆŐęÊœé_ÊŒĆcËûÍŹÊÂęRÛÉœșÏŚś·ŚgĄ¶ĐĄŒsșČĄ·ĄŁłőžćÍêłÉÓÚôŃžëxŸ©ÖźÇ°ŁŹÒîÄ궚žćÓÚVÖĘ���ĄŁ1924 Äê9 ÔÂ15 ÈŐ(chuš€ng)Śś”ÄĄ¶ÇïÒ襷éșÎłöŹF(xiš€n)ÁËžú1926 ÄêČĆŐęÊœÖűÊÖ·Śg”ÄĄ¶ĐĄŒsșČĄ·ÓĂŐZÏàœü”ÄĄ°ÆæčÖ¶űžßĄ±ß@Ò»ÆæáÈĐȚȚo����Łż
ß@ȹȻÆæčÖ����ĄŁÄ1906 Äêé_ÊŒ”œôŃž(chuš€ng)ŚśĄ¶Ò°ČĘĄ·”Ä1924Äê����ŁŹéôŃžËùÉîÛ”ÄĄ¶ĐĄŒsșČĄ·ÒŃœ(jš©ng)°éëSËûŐûŐû18 ÄêĄŁÔÚß@18 ÄêÀï����ŁŹôўȻrÏ딜ĄąéŚxÉőÖÁŽòËă·ŚgĄ¶ĐĄŒsșČĄ·���ĄŁëmÈ»ôŃž(shšȘ)ëH·ŚgĄ¶ĐĄŒsșČĄ·ÊÇÔÚ1926 Äꔜ1927 ÄêÖźég���ŁŹ”«ÔÚôŃž(chuš€ng)ŚśĄ¶Ò°ČĘĄ·rŁŹĄ¶ĐĄŒsșČĄ·”ÄÔS¶àÈ(nšši)ÈĘÒŃ ÊìÓÚĐŰ����ŁŹôŃžÓĂÖĐÎÄ·Śgß@Đ©È(nšši)Èʔĥ°žčžćĄ±ÒČÔçÒŃŽòșĂÁË����ĄŁĘ^șÏÀí”ÄÍÆyÊÇŁșß@Đ©·Śg”ÄĄ°žčžćĄ±°”ÖĐŽßÉúÁËÖTÈ祰ÆæčÖ¶űžß”ÄÌìżŐĄ±”ÄȘ(dšČ)ÌŰĐȚȚo���ĄŁ
ôŃž¶àŽÎÌᔜĄ¶ĐĄŒsșČĄ·Œ°Æä·ŚgĄ¶ĐĄŒsșČĄ·”Äœ(jš©ng)ß^���ŁŹŚăÒÆäÏČÛșÍÖŰÒ”ÄłÌ¶ÈĄŁ1906 Äê3 ÔÂôŃžÄÏÉĆ_át(yš©)W(xušŠ)���ŁżÆW(xušŠ)ĐŁÍËW(xušŠ)»Ű|Ÿ©����ŁŹÈë|Ÿ©Ș(dšČ)ÒĘŐZW(xušŠ)ț”Ä”ÂŐZW(xušŠ)ĐŁ���ŁŹ”«ÆœrÖśÒȘßÊÇŚÔĐȚ����ŁŹËŃŒŻéŚxÍâűÎÄW(xušŠ)ŚśÆ·����ŁŹÒÔĄ°Ìáł«ÎÄËß\(yšŽn)ÓĄ±Łš·ŚgșÍŚöŐÎÄŁ©���ĄŁ»Ű|Ÿ©ÖźșóČ»ŸĂ����ŁŹËûŸÍÔÚÙÓÚÉńÌï
^(qš±)Ćfű·»ŁéTó”Àłö°æĐĆÏą”Ä”ÂÎÄżŻÎïĄ¶ÎÄW(xušŠ)”Ä·ŽíĄ·ŁšDas Literarische EchoŁ©ÖĐŚx”œßxŚg”ÄĄ¶ĐĄŒsșČĄ·”ÚÎćŐÂŁŹĄ°·ÇłŁÉńÍùĄ±���ŁŹëSŒŽÍĐÍèÉÆű”êÄ”ÂűÙÙIAnna Fles ĆźÊż”Ä”ÂÎÄŚg±ŸŁŹĄ°ŽóŒsÈęÔÂÖźșó���ŁŹß@űŸÓÈ»ÔÚÎÒÊÖÀïÁËĄ±���ĄŁ ôŃžșóíĘ^ÔçÌᔜĄ¶ĐĄŒsșČĄ·ŁŹÊÇ1921 Äê11 ÔÂ10 ÈŐ·ŚgÛÁ_ÏÈçæĄ¶ô~”ıŻ°§Ą·ÖźșóËùŚ«Ą¶ŚgŐßžœÓĄ·ŁșĄ°ß@Ò»ÆȘŠÓÚÒ»ÇĐ”ÄÍŹÇé���ŁŹșÍșÉÌmÈËÌ@ńûŁšF.Van EadenŁ©”ÄĄ¶ĐĄŒsșČĄ·ŁšDer Kleine JohannesŁ©îHÏàî����Ą���ŁĄ±ÔÚ1925 Äê3 ÔÂÎŽĂûÉçłö°æ”ÄĄ¶żà”ÄÏóŐśĄ··â”Śžœä”ÄôŃžËùłö°æVžæĄ¶ĄŽÎŽĂû
ČżŻĄ”ÊÇÊČĂŽ����ŁŹÒȘÔőÓŁżĄ·ÖĐÒŃœ(jš©ng)îA(yšŽ)žæÁËĄ°Ą¶ĐĄŒsșČĄ·���ĄŁșÉÌmŚśŒÒÍûÌ@ńûŚśÉńĂŰ”Ä(shšȘ)”ÄÍŻÔÔ����ĄŁôŃžŚgĄ±����ŁŹß@ÒČŸÍÊÇĄ¶ĐĄŒsșČÒęŃÔĄ·ËùÖ^Ą°Ç°ÄêÎÒŽ_ÔűQĐÄŁŹÒȘÀûÓĂÊîŒÙÖĐ”Äčâê���ŁŹŐÌÖűÒ»±ŸȚo”䥱·ŚgĄ¶ĐĄŒsșČĄ·���ĄŁ”«Ö±”œ1926 ÄêÏÄôŃžëxé_±±Ÿ©ÖźÇ°ŁŹČĆŐęÊœĆcęRÛÉœșÏŚśŒÓŸoŚgłöłőžć���ĄŁ1927 ÄêÔÚVÖĘ���ŁŹœKÓÚ{Ò»ŒșÖźÁŠžÄ¶šŚgžćĄŁ
ß@Ö»ÊÇôŃžœÓÓ|���ĄąŐ?wšŽ)șÍ·ŚgĄ¶ĐĄŒsșČĄ·”ÄÈôžÉÖŰÒȘrégč(jišŠ)üc(dišŁn)����ŁŹËûÆœr”ąŚxĄ¶ĐĄŒsșČĄ·»òÔÚÒâŚRșÍoÒâŚRÀïââ¶ÈĄ¶ĐĄŒsșČĄ·ŁŹČąoÎÄŚÖÓä����ŁŹ”«1924 Äê9 ÔÂ15 ÈŐ(chuš€ng)ŚśĄ¶ÇïÒ襷֟ǰŁŹôŃžéLrégÏČÛ����ĄąéŚxĄąîA(yšŽ)ä·ŚgĄ¶ĐĄŒsșČĄ·���ŁŹÄËÊÇÒ»Č»ÈĘșöÂԔıłŸ°ĄŁ
±ËùÖÜÖȘ���ŁŹôŃžÄČ»ÂÓÈËÖźĂÀ���ŁŹżÉąŚÔŒș”ÄÖűŚg而śwÔÚeÈËĂûÏÂĄŁŒÈÈ»ôŃž·ŽÍ(fšŽ)(qišąng)Ő{(diš€o)ęRÛÉœŠĄ¶ĐĄŒsșČĄ·ÖĐŚg±ŸłőžćŰ«I(xiš€n)ÁŒ¶à���ŁŹéșÎŚîœKßxńȘ(dšČ)ÁąÊđĂû���ŁŹ¶ű]ÓĐžúęRÛÉœÂ(lišąn)Êđ����ŁżôŃžËœ”ŚÏÂșÍęRÛÉœêP(gušĄn)ÓÚĄ¶ĐĄŒsșČĄ·ŚgŐßÊđĂûÓĐșÎŒs¶š����ŁŹÉĐŽęŃĐŸżĄŁß@ŒțʱŸÉíÖÁÉÙÒČÄÒ»È(cšš)Ăæï@ÊŸôŃžŠËû±ŸÈË·ŚgĄ¶ĐĄŒsșČĄ·”Ğ߶ÈÖŰÒĆc·ÇÍŹÒ»°ă”ÄͶÈë����ĄŁŁšôŃž·ŚgĄ¶č€ÈËœ»ĘÂÔ·òĄ·ÒČÔű”Ă”œęRÛÉœĄ°ÔS¶àÖžüc(dišŁn)șÍĐȚŐꥱŁŹ”«ČąČ»Ïń·ŚgĄ¶ĐĄŒsșČĄ·ÄÇÓÓĐéLrég”ÄșÏŚś���ĄŁŁ©
ôŃž1927 Äê9 ÔÂ25 ÈŐĄ¶ÖÂĆ_ìoȚr(nšźng)Ą·ĐĆŐfŁșĄ°ÖZŰ Ùpœđ����ŁŹÁșąłŹŚÔÈ»Č»Ćä���ŁŹÎÒÒČČ»Ćä���ŁŹÒȘÄĂß@ćXŁŹßÇ·ĆŹÁŠ���ĄŁÊÀœçÉϱÈÎÒșÔČśŒÒșÎÏȚ���ĄŁËû”ĂČ»”œ����ĄŁÄ㿎ÎÒŚg”ÄÄDZŸĄ¶ĐĄŒsșČĄ·����ŁŹÎÒÄÇÀïŚö”ĂłöíŁŹÈ»¶űß@ŚśŐߟÍ]ÓДÔœ����ĄŁĄ±1936 Äê2 ÔÂ19 ÈŐĄ¶ÖÂÏÄśœ(jš©ng)Ą·ĐĆÓÖŐfŁșĄ°ÎÒËùŚgÖű”Äű����ŁŹeŒäÉÏ����ŁŹŒ°ŸŚg”ÄŁŹÎ©Ą¶ÒęÓńŒŻĄ·Ą¶ĐĄŒsșČĄ·Ą¶ËÀ»êì`Ą·Èę·NÉĐŒŃ���ŁŹe”ÄœÔĘ^Ćf���ŁŹÊ§ÁËrЧ���ŁŹ»òČ»ŚăÓ^ŁŹÆä(shšȘ)ÊÇČ»±ŰżŽ”Ä����ĄŁĄ±°ŃĄ¶ĐĄŒsșČĄ·”Ä·ŚgÌᔜșÍĄ¶ÒęÓńŒŻĄ·Ą¶ËÀ»êì`Ą·ÍŹ”Ȟ߶È����ŁŹŚăÒôŃžŠß@í(xiš€ng)·ŚgĐĐéžńÍâ”ÄÖŰÒĄŁÎÒÉőÖÁÒòŽËŃÒÉĄ¶ÈęÊźÄêŒŻĄ·”Ú¶ț·ĘĄ°ÄżäĄ±ÖĐÖÁœńÈÔÈ»±ŐfŒŒ”ÄĄ°ÆđĐĆÈęűĄ±���ŁŹ»òÔSŸÍÊÇÖžĄ¶ÒęÓńŒŻĄ·Ą¶ĐĄŒsșČĄ·Ą¶ËÀ»êì`Ą·”Ä·Śg����ĄŁ
ôŃžŐfĄ¶ĐĄŒsșČĄ·ÄËĄ°oí”ÄÔ����ŁŹłÉÈË”ÄÍŻÔĄŁÒò?yš€n)錜Őß”ÄČ©ŚRșÍĂôžĐ����ŁŹ»òŐߟčÒŃłŹß^ÁËÒ»°ăłÉÈË”ÄÍŻÔÁËĄ± ����Ą���ŁĄ¶ĐĄŒsșČĄ·ŠôŃžÈË(chuš€ng)Śś”ÄÓ°íœ^Č»ÖčÓÚ͏饰łÉÈË”ÄÍŻÔĄ±”ÄĄ¶łŻ»šÏŠÊ°Ą·ŁšÓÈÆ䥶İÙČĘ@”œÈęζűÎĘĄ·Ł©����ŁŹÒČȘ(yš©ng)Ô°üÀšÒ»Đ©ësÎÄșÍÉąÎÄÔŒŻĄ¶Ò°ČĘĄ·���ĄŁ
W(xušŠ)ŐßÔçŸÍŚąÒ├ÔÚ(chuš€ng)ŚśÀíÄîșÍ·œ·šÉÏ����ŁŹĄ¶Ò°ČĘĄ·ÉîÊÜôŃžËùŚgNŽš°ŚŽćĄ¶żà”ÄÏóŐśĄ·”ÄÓ°í����ŁŹËùÖ^Ą°ÉúĂüÁŠÊÜÁËșÒÖ¶űÉú”Äżà°ĂÀÄËÊÇÎÄ˔ĞùèÜĄ±ĄŁŸßów”œżÉÄÜÄß@·œĂæÓ°íôŃž(chuš€ng)ŚśĄ¶Ò°ČĘĄ·”ÄÓòÍâŚśÆ·���ŁŹtÍšłŁÏČgÄĂĄ¶Ò°ČĘĄ·ôŁšËùÖ^Ą°ôÆßÆȘĄ±Ł©ĆcĄ¶ÍÀžńÄù·òÉąÎÄÔĄ·���ĄąÏÄÄżÊțÊŻĄ¶ôÊźÒ襷Ïà±È����ĄŁÆä(shšȘ)Ą¶ĐĄŒsșČĄ·È«űôÖźÌO¶à����Ą���ŁĄ¶ĐĄŒsșČĄ·Äî^ÖÁÎČŸÍÊÇÒ»ČżÓôÖźű���ŁŹžś·NȻ͏”ÄôŸłœÓőà¶űÖÁĄ����ŁĄ¶ĐĄŒsșČĄ·žúĄ¶Ò°ČĘĄ·ÔÚô·œĂæ”ÄÏàËÆÖźÌŁŹßh(yušŁn)ßh(yušŁn)łŹß^Ą¶ÍÀžńÄù·òÉąÎÄÔĄ·șÍÏÄÄżÊțÊŻĄ¶ôÊźÒ襷����ĄŁ
Âä(shšȘ)”œŸßówÆȘŐ”ÄÁąÒâĆcÇČÔ~ÔìŸäŁŹłęÁËÉÏÊöĄ°ÆæčÖ¶űžß”ÄÌìżŐĄ±ÖźÍâ����ŁŹßÓĐĄ°ĐęșĄ±œoĐĄŒsșČÖvÊö”ÄÔS¶àĄ°șĂ”ÄčÊÊÂĄ±ŁŹÒČČÉÈĄżáËÆĄ¶Ò°ČĘĄ€șĂ”ÄčÊÊÂĄ·ÄÇ·NĂÜŒŻĆĆ±È”ÄŸ°ÎïĂè����ĄŁĐĄŒsșČĐŃíÖźșó���ŁŹ±MčÜÊÖÀïÄĂÖűÄôÖЧí”ÄÎïŒțŁŹ
sÈÔÈ»ŠôÖĐ”ÄĂÀșĂœ(jš©ng)vÒÉĐĆ
ą°ëŁșß@ÒČșÜÏńĄ¶șĂ”ÄčÊÊÂĄ·����ĄŁ
ĄĄ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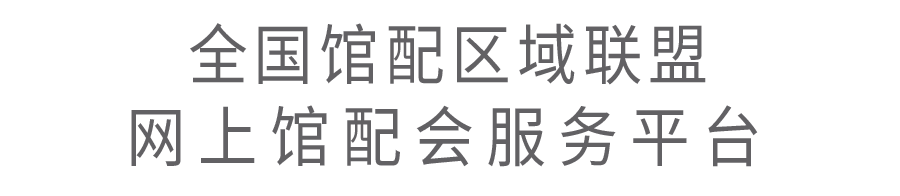
 űÎÍÆË]
űÎÍÆË] ĐÂűÍÆË]
ĐÂűÍÆË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