╣┬¬ÜÊ▓╩ÃÊ╗ÀN├└
┴_¢¿Èã
┼c¥®╚¬¤╚╔·ıJÎRÊТø(j¿®ng)ÂÓ─Ûú¼╦¹òr│úðª╬¹╬¹ÁÏ©·╬Êıfú║╩▓├┤òrÚgËð┐ı░��í����ú┐üÝÈã╠ý║ú┼¦£Ï╚¬ú¼▀@└´Á─¡h(hu¿ón)¥│▓╗Õe���ú¼╔·æB(t¿ñi)║├,╩Ã╠ý╚╗Ч░╔����íúÁ½òrÍ┴¢±╚ı��ú¼╬Ê╚Èø]╚Ñ▀^Èã╠ý║ú�ú¼Ê▓ø]╚Ñ┼¦▀^£Ï╚¬ú¼Á╣╩ÃÙSÍ°òrÚgÁ─═ãÊã����ú¼╬Ê®╚¬¤╚╔·Ëð┴╦È¢üÝÈ¢ÂÓÁ─┴╦¢Ô┼cıJͬ�����íú
╚þ╣¹ıf╚╦▓┼ú¼╬ʤ٥®╚¬¤╚╔·┐¤Â¿╩Ã╚╦▓┼����íúÈþÈ┌╚f╚╦²R▒╝¬Ü─¥ÿ‗Á─òr┤·ú¼╦¹═¿▀^ÎÈ╝║Á─┼¼┴ª��ú¼¦p°ÊÎ┼eÁÏ┐╝╔¤Íðîú����ú¼Ê▓îì¼F(xi¿ñn)§Ä¶~╠°²êÚTÁ─┐þÈ¢íúÊ▓ÈS±╠ýÁ──Û¦pîWÎËüÝıf�����ú¼©ðËX┐╝╔¤Íðîú▓╗╦Ò╩▓├┤���ú¼Á½îª60─Û┤·│÷╔·Á─╚╦üÝıf��ú¼┐╝╔¤Íðîúàs▓╗Í╗╩ÃôÝËðÊ╗ÅêÚLã┌´êã▒─Ã├┤║åå╬���íú
╬Ê┼c¥®╚¬¤╚╔·Ê╗ã┼─▀^ııã¼���ú¼╦¹└¤©·╬ÊÍvú¼Ê¬▓╗öÓ╠ß©▀ÎÈ╝║Á─özË░╦«ã¢�����ú¼Á├¤‗╬Êéâ─Û¦p╚╦îW┴ò�����íú╬ÊÙm╚╗É█║├özË░�ú¼Á½ÀQ▓╗╔¤╩Ãîú╝Êú¼┐╔├┐┤╬Ê╗ãözË░�����ú¼¥═ò■¢╗┴¸Ê╗ð®╝╝ðgåû¯}����ú¼àóöÁ(sh¿┤)▀\Ë├ú¼Ðð¥┐╚þ║╬▀x¥░����íóÿïêD����ú¼¢╗┴¸özË░ð─Á├�íú
╚Ñ─Û─Û─®ú¼╦¹┤‗ÙèÈÆ¢o╬Ê�����ú¼ıfÎÈ╝║¤Ù│÷üÝÊ╗▒¥ðíâÈÎË�ú¼îóÎÈ╝║▀@ð®─ÛîæÁ─Èè�����íóÈ~��íó┘x╔§Í┴Ú║┬ô(li¿ón)Á╚¢Y╝»│÷░µ�����ú¼¤Ùı¸Ã¾╬ÊÁ─ÊÔÊè�íú╦¹ıfÎÈ╣ñθÊÈüÝú¼▓╗╣▄╩ÃÈ┌ð¹é¸▓┐▓┐ÚT▀Ç╩ÃÈ┌╩ÀÍ¥▓┐ÚT�ú¼▓╗╣▄╩ÃÎÈ╝║Î÷©©ËH▀Ç╩Ã║¾üÝÎ÷áöáöú¼Í╗ʬËð┐ıËÓòrÚg�ú¼▀Ç╩ä▓Üg©¢Ë╣´LÐ┼�����íó╠¯È~θ┘x���íóʸÈèθîªÁ─íú
ÍT╚þ2011─Û12È┬�����ú¼╦¹╚ÑÈã─¤Â²║ú���ú¼ÊèÁ¢ðÒ├└´L╣Ô�����ú¼¾w‗×░ÎÎÕ´LÃÚ�����ú¼Èè┼d┤¾░l(f¿í)��ú¼┐┌ı╝Ê╗¢^ú║²║ú´L╣Ô└CÕ\¥d����ú¼╔n╔¢ýF©Â║╔±¤╔íú╚╦╬─░ÎÎÕ´LÃÚðÒ���ú¼▒┌«ïü└ñðÊ©ú╠ý����íú©±┬╔╬Ê▓╗║├Èuâr���ú¼îìÈÆîìıf�ú¼╬Êéâ70─Û┤·│÷╔·Á─╚╦���ú¼îª┬╔ÈèÁ─░Ð╬ı▀h▓╗╝░ÊÈÃ░┴╦í�����ú┐v╩╣¢±╠ýÅ─╩┬│÷░µ�ú¼╚È▓╗©ÊıfÎÈ╝║╩Ãîú╝ÊíúÁ½╬Ê─▄¾wò■Á¢ÈèÁ─ÊÔ¥│���ú¼║▄├└║▄├└���íú¤±ãõÍðË├Á¢Â║ÎÍ��ú¼îª¢^┤¾ÂÓöÁ(sh¿┤)╬─╚╦─½┐═üÝıf�ú¼╩Ã▓╗ò■ÙSÊÔË├Á─�����ú¼╗‗╩éðËX¢ÁÁ═ÈèÁ─ãÀ╬╗��ú¼╗‗╩éðËX▀^Ë┌¦p┬╩��ú¼Á½¢ø(j¿®ng)╦¹Ë├üÝ�ú¼©ðËX¢¡╔¢╚þ┤╦ÂÓï╔ú¼╚╦╔·╚þ┤╦├└║├��ú¼¦pÃ╬Ê╗³cËÍ║╬À┴����ú┐
È┘ıf2008─Û7È┬ú¼ÅVû|╩í╬─├¸¢¿ÈOò■Îh¼F(xi¿ñn)ê÷��ú¼╦¹╠¯┴╦Ê╗╩ÎÈ~íÂ▓╔╔úÎË·ãÀ¤╔╠ÊíÀú║╬─├¸╗¿ãGÏS¢¡┼¤��ú¼ã¼ã¼╔¢Ã���ú¼╔½¥GË═Ë═���íú╩ý═©·ù╠Ê░Ð┐═┴¶��íú«ö─Û═§─©¾┤╠ÊÐþ�����ú¼¤╔Á█├╔ð▀�íú╬ÊÁ╚║╬þ��ú┐╔ý╩Í╠ÊüÝ┐┌©ú│Û�����íúÎxÍ«┤╦È~����ú¼Îî╬Ê©ð┐«���ú¼ð┬ÏS¢¡┼¤▀Çıµ╩ÃËðÊ╗éÇ╩└═Ô╠ÊÈ┤�íó╚╦Úg¤╔¥│Т�íú╠Ïäe╩ý═©·ù╠Ê░Ð┐═┴¶¥▀Ëð«ï²ê³c¥ªÍ«╣ªðºíú╬Ê╩Ã┐┤íÂ╬¸Ë╬ËøíÀÚL┤¾Á─ú¼îª¾┤╠ÊÐþËí¤¾¯H╔¯�����ú¼îO╬‗┐ıÊ‗×Ú═Á│È┴╦ÄÎéǾ┤╠Ê°╚Ã│÷Ê╗▀B┤«Á─┬Úƒ®�ú¼¢K▒╗╚þüÝÀεë║È┌╬ÕÍ©╔¢¤┬íú╬ÊÈ┌¤Ù���ú¼╚þ╣¹îO╬‗┐ıͬÁ└ð┬ÏS¢¡┼¤Ëð─Ã├┤├└¹ÉÁ─ÁÏÀ¢���ú¼Í¬Á└Ëð·ù╠Êú¼╦¹▀Çò■╚Ñ═Á¾┤╠Êåß���ú┐╔±ÈÆÜw╔±ÈÆ����ú¼ÈO¤ÙÜwÈO¤Ù�����ú¼Á½┤╦È~¢o╬ÊÁ╚─Û¦p╚╦┴¶¤┬ƒo¤Ì¤Ù¤¾Á─┐ıÚg����íú
¥®╚¬¤╚╔·ÀQ▓╗╔¤┤¾╣┘ú¼Á½È┌═¼îWÐ█└´ú¼┐¤Â¿╩Ã╣┘���íúÈ┌Ê╗éÇ┐h│Ã�ú¼─▄╣┘Í┴┐h╬»ð¹é¸▓┐©▒▓┐ÚL�����íó╬─┬ô(li¿ón)͸¤»����íó╩ÀÍ¥Ìk͸╚╬ú¼È§├┤▓╗╦Ò╣┘─Ï����ú┐Á½╦¹╩╝¢Kıfú║╬Ê▓╗╩Ã╣┘ú¼╬ÊÍ╗╩ÃÈ┌©╔Ê╗À¦╣ñθ���ú¼¢M┐ùðÞʬ╬Êòr��ú¼╬Ê¥═░l(f¿í)Ê╗ÀÍ╣Ô��íóÊ╗À̓߅…°╦¹îæÁ─íÂ╔·▓ÚÎË·╚²╩«─Û¥█╩ÎíÀàs═©┬ÂÎÈ╝║îª═¼îWÁ─ƒo¤ÌÊ└æ┘┼cîªðúê@Á─ƒo¤ÌæÐ─¯ú║«ö─Û═¼îWòrú¼┤░¤┬ͬ║«ÊÔ��íúè^┴ª▀^å╬ÿ‗ú¼ı╣═¹┴ÞÈãÍ¥���íú╚╦╔·Í«┬├�����ú¼ıµı²─▄ÎîÎÈ╝║ßîæÐ▓╗¤┬Á─▓╗═Ô║§Ëð╚²�����ú¼Ê╗╩é©─©ðÍÁ▄Í«ÃÚ����ú¼Â■╩Ã═¼îW║├ËÐÍ«ÃÚ����ú¼╚²╩Ã¥╚┐Ó¥╚ÙyÍ«ÃÚíú°¥®╚¬¤╚╔·Å─ı■║¾��ú¼▓╗═³│§ð─����ú¼┼c═¼îW▒ú│Í║▄║├Á─╗ÑäË┼c¢╗┴¸ú¼ãõîì╩Ã║▄ÙyÁ─�����íú╚╦╔·┐ÓÂ╠ú¼─▄ËðÄÎéÇ╚²╩«üÝ╗Ï�ú┐°╦¹éâú¼È┌«àÿI(y¿¿)╚²╩«─Û║¾─▄¥█È┌Ê╗ã����ú¼┤░¤┬ͬ║«ÊÔú¼▀Ç╩Ã║▄┴¯╚╦©ðäËÁ─�����íú
▀@ð®─Û╬ÊÎ÷│÷░µ���ú¼×Ú╚╦Î÷┴╦ƒoöÁ(sh¿┤)╝ÌÊ┬��ú¼Á½╬ÊÊ╗Í▒À┤îªéÇ╚╦│÷ò°�����ú¼©¨▒¥È¡Ê‗╩Ã╬─îWθãÀ▓╗║├õN╩█����ú¼Â°ÈèÈ~©³╩Ã÷©▀║═╣Ð�����íú«ö┐┤Á¢¥®╚¬¤╚╔·Á─θãÀòr�����ú¼▓┼ËXÁ├╦¹îªÈèÈ~╚þ┤╦ƒßÉ█�����ú¼╚þ┤╦ê╠(zh¿¬)Í°��ú¼©³ø]¤ÙÁ¢╦¹îæÁ─ÈèÈ~╚þ┤╦¢ËÁÏÜÔ����íú«ö╦¹ıÊ╬Êθð‗òrú¼╬ÊÍ╗╩Ãıf├¸����ú¼╬ÊÀÃ├¹╚╦┤¾╝Êú¼┼┬╬ÊθÁ─ð‗äe╚╦▓╗ıJ┐╔�ú¼Ë░Ýæãõò°Á─ãÀ╬╗┼c┘|┴┐íúÁ½╦¹ıf�����ú¼╬Ê─▄͸¥ÄíÂ×t¤µ╬─╗»íÀÙsÍ¥ú¼─▄│÷░µíÂ╚╦╔·╦─╩«─ÛíÀîúÍ°�ú¼─▄͸¥Äí¼F(xi¿ñn)┤·æ¬Ë├╬─îæθíÀ┤¾îW¢╠▓─ú¼ÊÈ╬ÊÁ─ÀÍ┴┐��ú¼Î¸ð‗ë‗©±┴╦�íú╬ÊÊ▓▓╗ͬÁ└¥┐¥╣ë‗▓╗ë‗©±ú¼¥═îæ┤╦╬─����ú¼ÖÓÃÊ×Úãõð┬θ│÷░µÎ¸×Úð‗░╔íú
╬ÊÎÀþ╬─îWÄÎ╩«─Û┴╦����ú¼Ê╗Í▒ËðÀN┐Óðð╔«Á─╬ÂÁ└ú¼©ðËX║▄╣┬¬Ü��ú¼Â°ÈèÈ~©³╝Ë╣┬¬Ü��íú«ö╬Ê░Ð▀@ã¬ð‗îæ═ÛÁ─òr║‗�����ú¼╬Ê║▄¤ÙͬÁ└�����ú¼¥®╚¬¤╚╔·╚þ║╬├µîªÈèÈ~ĺüÝÁ─╣┬¬Üú┐╩ÃÊ‗×Ú╣┬¬ÜÊ▓╩ÃÊ╗ÀN├└åß����ú┐
ú¿┴_¢¿Èã¤Áû|¦©╩ð×t¤µ╬─╗»é¸▓ÑËð¤Ì╣½╦¥┐é¢ø(j¿®ng)└Ýíóû|¦©╩ð▒╚▒╚Ëí╦óËð¤Ì╣½╦¥┐é¢ø(j¿®ng)└Ý��íóíÂ×t¤µ╬─╗»íÀ͸¥Ä�����ú¼│÷░µ?zh¿¿n)Ç╚╦îúÍ°íÂ╚╦╔·╦─╩«─ÛíÀú®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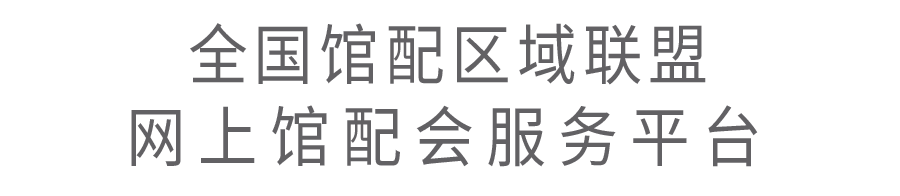
 ò°å╬═ã╦]
ò°å╬═ã╦] ð┬ò°═ã╦]
ð┬ò°═ã╦]